摘 要:对某精炼钢包底部冲击区经100次连铸后的AMC耐火砖进行了分析。利用X射线衍射、X射线荧光光谱仪、反射光学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能量色散X射线光谱仪、密度和气孔率测量以及压汞法分析了炉渣、未使用的耐火材料和炉渣+钢侵蚀砖的化学和物理特性。侵蚀过程产生了一种特定的微观结构,其特征是:由二次尖晶石+钢+液相组成的厚而不连续的渣层;在炉渣/耐火材料界面处由铝酸钙+钢+液相组成的致密、裂化的连续厚渣层;在该层旁边,是一个具有均匀微观结构的宽致密层,其中刚玉骨料和尖晶石晶体被拉长的CaAl12O19晶体连接在一起。这些反应层的形成构成了一道屏障,有效地抑制了大量熔渣的渗透,从而降低了磨损率。根据凝聚相平衡图进行了热力学计算,以进一步研究侵蚀机理。
1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钢包底部及渣线部位使用铝镁碳砖(Al2O3-MgO-C,缩写为AMC),已推广至整个炼钢工业。本文对某炼钢厂钢包底部冲击区的AMC用后残砖进行了分析,并着重研究了钢包冲击区AMC砖的渣侵蚀问题,认为AMC砖的碎裂无疑会导致耐火材料的损坏。利用几种分析技术模拟耐火材料在使用期间的经历,从而得出可能的降解机理。热力学模拟是研究耐火材料的有效工具,因为长时间暴露于使用条件有利于系统(耐火材料/炉渣)向热力学平衡方向发展。
2 材料和方法
在钢包底部冲击区使用的AMC残砖,标记为AMC4。图1示出了AMC4砖的用后残砖,渣仍附着在砖的热面(工作面)上。

图1 用后AMC4砖残砖
经过1 0 0次连铸后钢包中仍有A M C 4残砖。生产的钢成分大致如下:C 0.0 8%~0.4 5%,Mn 0.6%~1.5%,Si 0.2%~0.5%,Al 0.01%~0.04%。在钢包底部与AMC砖之间的连接处用耐火泥浆填充。为了分析AMC4砖在使用过程中的降解情况,采用了多种技术对用后AMC4砖进行了全面分析,结果列于表1。自垂直于用后残砖的加热面切下两片厚度约25 mm的切片,并在每个切片上平行于热面切割三个切口,得到三个厚度为20 mm的试样。这些棱柱状试样(20 mm×20 mm×25 mm)被标记为PM1、PM2、PM3和PM4,代表了耐火砖与加热面的不同距离,见图2(PM1包含加热面和粘附的熔渣)。采用多种技术对用后试样(PM1~PM4)进行分析,以评估用后耐火材料的降解情况。
注:a:Fe2O3,SiO2,CaO,TiO2;b:Vp—<1μm气孔体积百分比;c:πa—显气孔率;d:Kp—渗透性。
3 结果与讨论
与图3(b)中未使用的AMC4砖的特性相比,图3(a)中含有熔渣-耐火材料界面的PM5试样上观测到材料的磨损和脱碳,尤其是在热面上。砖的原始尺寸为10 cm×15 cm×25 cm,工作面面积为10 cm×15cm,用后残砖的长度约为11 cm,这表明在100次连铸后砖的磨损率大约为56%。

图2 用后AMC4砖的切片

图3 AMC4砖图
距热面约0.7 cm处出现熔渣和金属渗入,砖的质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该区域被分成两个部分:一个不同于原砖颜色的工作区域,表现出与炉渣的接触和脱碳;另一个扩展侵蚀区域,可以观察到钢渗透、裂纹及气孔形成。远离熔渣-耐火材料界面处,材料变化不大,仅检测到原始棕色聚集体的变色。这种现象可能与烧结镁砂或棕刚玉颗粒有关,是在钢包操作的高温条件下,砖中的Fe+2、Ti+2等杂质的氧化或迁移所致。表2列出了两种渣的组成,即钢包最后一个循环的中间部分(m渣)和附着在用后砖上的成分(a渣)。第一种炉渣为倒空钢包时与AMC4砖接触的熔渣。而a渣是砖被侵蚀后,残余液体冷却而形成的。因此,后者的氧化铝含量较高(高出约25%),这是由于AMC耐火材料以Al2O3为主要成分,这也是使用Urbain模型计算的黏度较高的原因。当熔渣与耐火材料反应时,黏度增加可能会阻止熔渣的渗透,有利于抗侵蚀。此外,a渣比m渣的FeO含量高,这可能是由于在钢包操作过程中熔融金属与液态渣混合所致。使用FactSage软件计算得到m渣的软化温度为1 256℃,高于该温度时熔渣将处于渗透耐火材料的状态。此外,由于成分变化,通过热显微镜测定的粘附渣的软化温度更高,为(1 369±5)℃。表3列出了AMC4砖从初始预热到出钢温度之间的平衡相。预热期间砖块的外表面与大气接触,因此模拟过程中没有额外加入氧气。100次连铸后达到平衡条件,预期在PM1~PM4中将发现这些固相。表4列出了在m渣冷却过程中形成的平衡相,这些固体与附着在熔渣中的固体相当。最后,作为计算步骤(CS)的函数,图4显示了在最临界条件下出现在耐火材料-渣系平衡中的主要相的演变,以及用Urbain模型计算出的液体黏度变化(图4c)。
表2 渣的特性分析

注:a:CaO/(SiO2+Al2O3)(质量比)。
表3 在700~1 700℃之间AMC4砖内的固相平衡%

注:a:非化学计量。
由表3可知,耐火材料各组分之间最大转变发生在7 0 0℃:O2不过量时,A l和S i与石墨反应形成碳化物,M g O与A l2O3反应生成尖晶石(MgO·Al2O3)。尖晶石的增多与Al2O3含量减少同时发生,这是由于Al2O3以固溶体形式结合到尖晶石结构中。由于动力学因素等原因,这些转变在实际材料中发生的温度稍高于1 000℃。因此,特别是在大量连铸之后,平衡条件可作为指导以了解耐火砖内部随温度升高而发生的变化。在用后试样的衍射图中检测出的晶相列于表5。
表4 m渣冷却过程中的平衡相

与热力学模拟结果一致,在每个试样中均检测到了尖晶石(MA),所有PM试样中均出现Al峰,而氧化镁仅在PM1和PM2中出现。尖晶石的强度与XRD中4个试样的峰值相似。Al4C3被预测为平衡相,因为当氧化剂存在时,它会迅速分解,或者与MgO反应形成尖晶石,这取决于未反应的AMC4在空气中的热演化。砖块在使用过程中的氧化条件很可能比平衡计算模拟中的更强。所有用后试样的金属硅X射线衍射峰都消失了,与表3一致,这种技术无法识别出其他含Si物相,如在平衡状态下应该存在的SiC。但实际上这最后一个固相是未使用的AMC4试样在1 600℃热处理时检测到的。另一方面,未使用的AMC4在空气中加热到1 400℃时观察到了莫来石,但这种情况下没有发现碳化物。据报道,1 100℃时Si颗粒表面的SiO2反应形成SiC,1 300℃时金属完全反应。研究认为,还有一些挥发过程,导致以玻璃硅形式存在的气态物质进一步凝结成孔。上述过程可根据用后试样中碳化硅的缺失(或痕量未检测出)来解释,表明在砖工作时冷面温度高于1 300℃。在钢包最后一次连铸时的发生几率较大,很大程度上缩短了砖的长度。而Si和中间体SiC在工作面氧化形成的SiO2会在液态渣中溶解。表5中试样的石墨含量与热力学模拟结果一致。据推测,组分初始含量的减少可能是它与Al和Si反应生成碳化物所致,石墨在PM1~PM4中的主衍射峰与未使用材料的主衍射峰强度相似。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方面,来自树脂热解的残余碳活性最强,但热力学模拟中未评估;另一方面,在AMC4中Si的存在增强了其抗氧化能力,特别在高温下,可能这是石墨在用后试样中持续存在的另一个原因。图5示出了未使用的和用后A M C 4材料的热谱图(TGA)。如前所述,未使用的AMC4质量减少是因为300~500℃下树脂挥发物消失,在600~800℃下石墨和残余碳的氧化。在500~800℃之间观察到碳氧化的质量损失,数值列于表6。
表5 用后试样中的晶相XRD


图5 未使用的和用后AMC4材料的热谱图(TGA) 表6 未使用和用后AMC4材料的质量损失(TGA)、体积密度和气孔率

注:a:从TGA曲线得到的在500~800℃下的质量损失。
PM1试样在500~800℃之间的质量损失最低,这是由于直接暴露在大气中(在最后一次预热时)和最高温度下工作面严重脱碳。发现PM2、PM3和PM4的碳氧化物质量损失均高于原试样,碳含量不仅维持了XRD分析中的原始水平,在使用过程中还有所增加。这一点在500℃和800℃以下的热处理中得到证实,热处理模拟了TGA时间表,对大块(3.5 g)的用后和未使用的试样进行了测试。此外,以较慢速度(0.125º/min)对未使用试样和用后试样进行了X射线衍射分析,在2θ范围内,刚玉的衍射峰位于25.50º(75%I/I0),石墨的主衍射峰则位于26.28º。通过对这些峰下面积的比较,证实了PM2、PM3和PM4中石墨峰的强度与原试样相比并没有显著降低。图6中碳含量的增加是在砖工作期间发生的,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在炼钢过程中砖所产生的热梯度,从约1 700℃的热面到较低温度的冷面,最后铸件的温度接近1 300℃,树脂热解产生CO2和CO,残余碳的反应以及石墨的氧化(至少应在预热过程中发生),由于该区域的较低温度,从热面向冷面移动。CO2和CO等气体可与MgO/Al2O3反应,生成低结晶度的反应产物,如碳化物、碳氧化物和无定形碳(炭黑),不易被XRD分析检测到。其中一些反应表现出碳含量的增加,具体如下:
相对于AMC4原始材料来说,用后试样质量损失以及在800℃左右时TGA曲线中的最小值向较低的温度转移,都意味着后生成的碳反应性更强。假设CO/CO2在热面的演化更大,并且这些气体应该向相反面迁移,那么碳的最大浓度应在砖内部出现。根据热谱图,这一最大值位于PM2中心距离最后一个热面3 cm处。在离工作面较远、温度较低的用后试样中,在平衡条件(表3)下并非所有的MgO都转化为尖晶石(表5)。由于MgO颗粒尺寸较大,在AMC4中尖晶石的形成程度低于MgO含量相似的其他AMC材料。考虑到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尖晶石数量在砖的长度方向上相似,工作面附近的用后试样中没有出现方镁石,不太可能是由于转化为尖晶石的程度较高,而是由于在另一个过程中消耗了MgO。由于该区域高温(约1 700℃)下固相的反应性相当高。例如,由于温度条件(T>1 200℃)加上较低的氧分压,氧化镁在较热的区域(PM1和PM2)可以通过碳热还原作用与碳发生反应,反应式为:2MgO(s)+C(s)→CO2(g)+2Mg (g)。可能Mg (g)没有再次氧化而从砖中逸出,亦或如果发生氧化,在工作面附近的试样中新的MgO没有同时增加该区域的尖晶石比例。在粘附渣的XRD衍射图中发现了以下结晶相,符合铝镇静钢精炼过程中Al2O3含量高的特性以及其三元碱度指数:C12A7(12CaO·7Al2O3)、C3A(3 C a O·A l2O3)、C A2(C a O·2 A l2O3)、MA(MgO·Al2O3)、CaO,C2S(2CaO·SiO2)、FeS2、Ca(OH)2、Mg(OH)2、MgO。其中,主要矿物相为C12A7和C3A。m渣在其凝固前的温度范围内的平衡态与矿物学组成的符合度较高。另一方面,a渣中钙和镁氢氧化物的鉴定是由于游离氧化钙(CaO)和游离氧化镁(MgO)作为平衡相在高温下形成,并由X射线衍射(XRD)检测到,易受湿度的侵蚀而引起的水化作用。熔渣容易与热表面分离,正是因为这些水合物具有显著的相关体积变化,从而导致破碎。这也是由于a渣中存在的水合物脱水而使PM1热谱图显示的质量略增高于100℃。图4中所包含的信息有助于理解炉渣和耐火材料在连续使用周期中的相互作用,这可能是它们降解的根源,但不完全是。停止侵蚀所需的计算步数(CS)被认为是材料耐蚀性的指标。考虑到这一点,如果将这一参数(CS=12)与模拟其他MgO含量相似的AMC材料在1 600℃(CS=3或4)下的侵蚀情况进行比较,高侵蚀磨损预计发生在使用条件下的AMC4砖。这些AMC材料在实验室测试中的腐蚀磨损约为10%。如图4(a)所示,第一个CS中的液体百分比非常高,几乎完全溶解了耐火材料的成分,因此,当钢包空时,预计熔渣在1 700℃下会对耐火材料产生严重侵蚀。在图4(c)中,液体黏度随CS的增加而变化,CS=0的值相当于m渣在1 700℃时的黏度。由于图4(b)中Al2O3含量增加(CS从27%增加到60%)和Fe+2/Fe+3含量减少(<10-3%),黏度值降低,趋于2.18泊,高于开始时的值。这意味着当熔渣渗入耐火材料时,其侵蚀性降低,有助于阻止侵蚀。作为Mg和Al液相饱和度的产物,热力学模拟预测MgAl2O4首先结晶,其次是(CS=4)CA6,从第4个计算步骤开始,液体主要成分的比例保持不变。在随后的步骤中,CA6的含量会增加,直到刚玉成为一个稳定相。根据表5数据可知,熔渣-耐火材料相互作用形成的固体仅在PM1中被识别:铝酸钙CA、CA2和CA6。热力学模拟结果表明,在最高操作温度(~1 700℃)下,只有后者在渣的侵蚀过程中生成。此外,在PM1中还检测到镁尖晶石,如图4(a)所示,镁尖晶石可能是耐火材料组分反应形成的,也可能是耐火砖与炉渣反应形成的。通过对扩展侵蚀区(PM5)的显微观察,可以得到炉渣与耐火材料界面更详细的图像。通过对钢渣反应区的显微组织和扫描电镜分析,证实了在钢渣和耐火材料界面形成了不同的反应层,如图6~图8所示。

图6 用后AMC4砖反应区(钢+熔渣/耐火材料)的界面图像
渣区:由富铝酸钙液相形成的厚度约200μm的不连续层,液相中含有少量[(Mg,Fe,Mn)(Al,Cr,Fe)2O4]尖晶石和钢的立方颗粒,见图6(a)。反应区由两层组成:一层厚度为500μm的连续致密层(图6),存在一个光滑区域,可能对应于CA2和液体。SEM和EDS分析用后砖的侵蚀区(图7,PM5)证实了反应产物的存在。经能量色散X射线微区分析,该层的平均组成约为:64%Al2O3,18%CaO,7%Fe2O3,6%SiO2,4%TiO2和1.4%MnO,见图7(a)。该组合物与铝酸钙(CA2)、钢和无定形相的存在相容,见图6(b)、图7(c)和图8。熔渣与原砖中的刚玉颗粒反应生成铝酸钙:Al2O3+液相→CA2。在纹理较少的区域,发现了一些与CA2和CA2S(钙长石)兼容的一些EDS点,同时检测出CA组成的点。在耐火材料的较深处,有一宽而多孔的层状结构,由长度约30μm、宽度约3μm的长条状晶体组成,并有角形孔隙,这可能与六铝酸钙晶体有关。SEM-EDS分析,发现有86%Al2O3,9%CaO,4%TiO2/SiO2。观察到未反应的刚玉骨料和钢及一些尖晶石富集区可能与原砖中存在的方镁石晶粒有关:MgO+液相→MgAl2O4。该区域基质反应完全,仍保留了最大刚玉聚集体的结构和成分(图7)。熔渣与刚玉反应形成典型的CA6针状晶体:Al2O3+液相→CA6。事实上,一些粗糙的氧化铝骨料保持其整体性可能与CA6层(间接侵蚀)的形成有关,该层介于耐火颗粒和液态熔渣之间。之后,侵蚀可能成为一个扩散受控制的过程,预计这种变化会导致侵蚀减速。

图7 熔渣+钢/AMC4反应区两个区域的FE-SEM显微照片

图8 熔渣+钢/AMC4耐火界面横截面的FE-SEM显微照片
热力学模拟结果表明,在1 700℃时,反应区内的CA2不是稳定相。为了解释二铝酸钙是如何出现在被侵蚀后的砖的最终微观结构中,还可以根据相平衡图来讨论二铝酸钙的侵蚀机理。AMC4耐材属于Al2O3-MgO-SiO2-C四元体系,当与炉渣发生反应时,其他组分如CaO和Fe也应视为构成6组分图的组件。但是考虑到整个系统的主要组成,可以用Al2O3-MgO-CaO凝聚相图来研究耐材与炉渣的反应。图9示出了1 650℃下Al2O3-MgO-CaO三元系统等温截面,这个温度略低于处理的最高温度。

图9 1 650℃下Al2O3-MgO-CaO三元系统等温截面相图
在侵蚀过程中,炉渣通过开口气孔和晶界渗透到耐火材料中,热面附近的炉渣溶解耐火材料并逐渐改变其成分,由m渣简化成分对应的点向图9中AMC4简化成分的方向移动,这造成耐火材料中氧化铝(Al2O3)、氧化镁(MgO)和尖晶石(MgAl2O4)部分溶解,以及CA6、MA、CA2晶体在耐火材料/炉渣界面的沉淀。考虑到这一结果,CA2结晶可能是在冷却阶段析出。此外,考虑耐火材料的不均匀性,它会导致材料成分的局部变化。图9中的R1和R2点代表不同MgO含量的AMC4区域,例如氧化铝聚集体和基质区域,分别含有氧化铝和氧化镁小颗粒。考虑到炉渣与各种耐材成分之间的连接线,反应路径首先经过CA2(R1)或MA(R2)的主要场,镁含量较高的耐火区将导致液相线上的截面点位于二铝酸钙场之下。因此,CA2或MA晶体分别在交点X和Y处开始析出。在初级晶体形成之后,第二次级相(MA或CA2)发生结晶,促使CA6形成。在热力学模拟中由于考虑了炉渣和耐材的整体化学成分和反应,因此炉渣与AMC4接触这一方面不能被考虑。CA2相和CA6相的形成使CaO在液相组成中逐渐减少,液相黏度增大。在这一点上,对耐材内部的侵蚀过程是由在Ca中耗尽的不具侵蚀性的熔体的扩散引起的。该熔体在氧化铝中迅速饱和,从而导致CA6和更多的MA形成。在炉渣界面上存在的相(MAs+液相;液相+CA2+MA;CA6+MA+A)是根据Al2O3富集区的相平衡图所预期的相。根据热力学计算及前文分析可知,MA尖晶石是在1 700℃形成的第一个稳定的固体;此外,该固体实际上是含有过量Al3+离子和少量铁(Fe2+/3+)的固溶体。SEM/EDS分析也证实了在扩展侵蚀区的MA尖晶石,在该固溶体中存在不同离子(Mn2+、Fe2+、Ti4+、Al3+)。众所周知,立方晶体结构中含有阳离子,因此在铁汇集的情况下有利于熔体黏度的增加。尽管无法确认SEM/EDS确定的尖晶石晶体的来源,它们可能是由耐材自身成分的反应原位形成的,但更有可能是对应于由MgO中的炉渣饱和而形成的(初级或次级尖晶石)。在1 000℃以上形成的原位尖晶石通常是细晶的,因此很容易被炉渣溶解。与反应区发现的部分侵蚀状态的刚玉聚集体相比,没有观察到MgO颗粒,这与热力学模拟预测一致,因为它不是一个平衡相。根据这些数据,方镁石在与渣接触过程中受到这种液体的强烈侵蚀,导致其完全溶解。根据热力学模拟,反应区识别出的CA在1 700℃时不是稳定相,也不是基于相图分析。考虑到这些固体可能是渣组成的平衡相,这可能是在冷却过程中在矿渣集中的区域形成的。此外,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模拟考虑了可溶解的耐火材料的所有组分,而实际上只有基质中最细小的颗粒才会首先溶解或更容易溶解,聚集体将与颗粒发生反应,正如分散在反应区的受攻击的氧化铝颗粒所显示的那样。最后,物种迁移的限制(动力学因素)在决定最终界面微观结构特征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用后碎片的热面上观察到了钢的渗透,还模拟了AMC4与熔融钢之间的接触(未额外加入O2,与钢中C平均含量)。因此,只有耐材自身成分之间的反应与耐材的冶金转变有关。结果表明,钢对砖磨损的贡献是由化学侵蚀外的机制造成的,如物理/机械效应。正如在扩展反应区所观察到的那样,钢水可能通过其促进裂纹的形成而对耐火砖造成损伤。如上所述,钢包在接收钢液之前先预热到1 100~1 300℃。在此温度范围,在空气中,材料的转变包括开口气孔率的增加,如图10所示,为不同温度下AMC4的PLC测试。表7为PLC测试的最后一个周期(3或5个周期)小于10μm的气孔尺寸分布。在第一次加热循环后气孔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1 000~1 400℃之间达到相似的值(在这最后的条件下,有证据表明烧结的最细的粒子)。在使用中也观察到了这种行为,从用后试样的显气孔率变化也表明了这一点。根据这些数据,AMC4砖的气孔率在第一次预热过程中随着到热面距离的增加而增加,随后气孔体积的变化速率可能减小。

图1 0 AMC4(空气中)及用后试样在PLC测试中显气孔率的变化
表7 PLC测试试样的孔径分布(小孔径<10μm)

表7中的数据表明,显气孔率的增加伴随着小气孔的加入而产生大的气孔,从而使气孔尺寸分布向更大的值偏移,在完整的孔径分布(包括>10μm的气孔)中也观察到了这一点。预计使用中的AMC4砖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同时由于这种类型的气孔的开放,在热面附近记录到的封闭气孔体积减少了。气孔率的所有这些变化(气孔体积和大小的增加,封闭的气孔打开)主要与树脂热解的第一步(发生在300℃左右的第一次加热阶段)中挥发分的消除以及不同物种的挥发有关,如前面讨论的碳的氧化。与气孔率的这些变化一起,这种AMC砖的承载能力发生了下降。因此,当砖块第一次受到钢射流的冲击时,液体可以穿透已经存在的开孔和裂纹,甚至产生新的碎片(侵蚀)。这是砖坯在钢包底部冲击区最关键的条件:钢水的冲击、突然的热变化(热冲击)和侵蚀。此外,随着钢包周期的热变化钢水滴落,膨胀和收缩的差异是热变化的结果。考虑到主相变的热膨胀系数是沿着砖的方向发生的(大部分是不可逆的),钢的热膨胀系数略高,约11×10-6℃-1,氧化铝的热膨胀系数为7.4×10-6℃-1,尖晶石的热膨胀系数为8.8×10-6℃-1,多晶石墨的热膨胀系数为7.8×10-6℃-1。由于这个原因,在整个使用过程中的膨胀-收缩循环将促进开裂,从而在钢包运行结束时有更多的钢或渣渗透。另一个与耐火材料本身开裂有关的过程是尖晶石形成,这与钢的渗透无关。当有炉渣存在时,具有各向异性膨胀特性的针状CA6的结晶,特别是如果在熔体的帮助下,是裂纹形成的另一个来源。表7所列出的气孔尺寸分布对应于在炉渣渗透中起重要作用的气孔。根据下面的公式,温度效应引起的中气孔直径增大有利于渣的渗透:式中:dl/dt为炉渣通过气孔(被认为是毛细管)的渗透率;l为炉渣渗透深度;r为气孔半径;∆P为毛细管吸力(随着孔径减小而增大);η为渣黏度。在较高的温度下,热面最容易被渗透,随着温度和孔径的减小,这种趋势减小。钙铝酸盐渣对AMC砖的降解机理论述如下。钢包底部冲击区的AMC砖在使用中遭受了严重损坏,损失了大约一半的初始体积。根据对这项工作所得结果的分析,提出了以下服役期间的降解机理:在第一个钢包循环前的预热中,耐火衬里在800~1 300℃下与周围大气直接接触。在这一阶段,整个砖结构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尤其是树脂溶解(大约300℃开始),导致开口气孔体积和孔径的增加,在靠近工作面的较热区域更为明显。因此,靠近砖表面的层其机械强度变弱。在等待过程中,耐火砖内部发生了其他化学和矿物学变化,特别是Al、Si和MgO的变化,其中一些变化有助于提高耐火砖的力学性能。尽管存在氧化气氛,石墨/残余碳的损失似乎并没有对耐材的降解产生显著影响。耐火材料首次在接近1 700℃的温度下接受钢液喷射,在这一过程中,耐材受到冲击、热冲击和侵蚀等热机械载荷作用。因此,外层和较弱层的材料就损失了。在这种情况下,钢水通过开口气孔和裂纹渗透到砖中,并可能打开新的气孔和裂纹,因此,加热和冷却循环可能会促进体积变化引起的损伤。在钢水浇注到中间包时,浮在钢表面的液态渣刚好在钢包周期结束时与耐火材料发生接触。有证据表明,炉渣穿透AMC4耐材并攻击最敏感的基质,包括较粗的颗粒,使它们部分溶解(如刚玉聚集体就是这样)或完全溶解(如方镁石和较细的刚玉颗粒)。在侵蚀过程中,液态渣(富含铝酸钙)与耐火材料的主要成分(Al和Mg)发生反应,形成各种不同的反应层:a)熔渣/耐火材料界面上由少量尖晶石[(Mg,Fe,Mn)(Al,Cr)2O4]颗粒+钢+液相形成的厚的不连续层;b)由CA6晶体形成的致密区,在未反应的刚玉集料和尖晶石颗粒之间形成致密的网络,有助于减小腐蚀的进一步加剧。这一层的形成可以构成一个屏障,有效地抑制了大量熔渣渗入脱碳耐火区。由于其他原因,如炉渣黏度增大、饱和最后凝固,这一过程也可能停止。六铝酸盐的形成(似乎经常发生)也可能对最外层造成机械损伤。钢包保持在高温(<1 300℃)下等待新的钢水装入。由于材料损耗,砖的长度减小,冷热面之间的热梯度变陡,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可知,砖的长度减小到原尺寸的56%,冷面温度可达1 300℃左右。
4 结论
通过用后分析,找出了造成钢包底部冲击区AMC砖破裂的主要原因,重点是渣蚀磨损。未使用的AMC砖的性能可以作为检测耐火材料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参考。热力学工具的使用有助于了解在钢包第一次加热时耐火材料组分之间的化学相互作用,以及在每个循环结束时砖和液态渣之间的化学相互作用。综合考虑所获得的信息,提出了AMC砖的可能降解机理。认为耐火材料磨损的主要过程如下:(1)预热阶段主要在树脂热解过程中由于挥发性物质的消除导致气孔体积和尺寸增大;由于本文研究使用的AMC砖(100次连铸),将上述4个过程重复作用,使得AMC砖的厚度减少了一半以上。结果表明,液态渣渗透到AMC砖中,实际上侵蚀了耐火材料组分。因此,耐火基质和部分细骨料(主要是方镁石)溶解在液体中。此外,如MgAl2O4(在固溶体中含有离子)、CA2和CA6结晶体等一些固体,最后阶段的层状形态可以作为侵蚀屏障。其他过程,如渣黏度的增加,也有助于阻止渣的侵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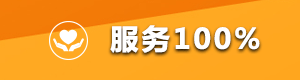

 易耐网公众号
易耐网公众号